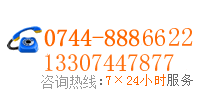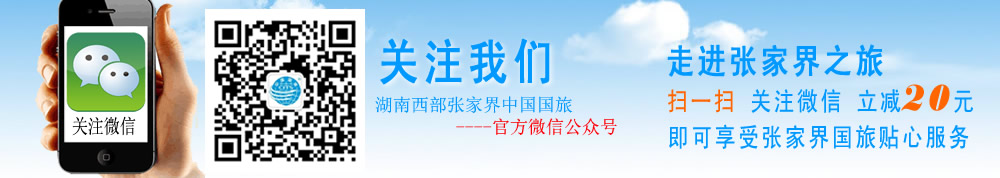去年三月和朋友去了凤凰,时值一周年,转载以前的文章以示纪念:
一袭单衣,匆匆跳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的开动的时候,我暗自松了口气,终于成行了。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地方已经不重要了,但我清楚的记得什么时候动的这个念头——去凤凰,走在那湿漉漉的青石板上,什么都想,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并对此具有无尚之爱的人,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仅仅因了美丽的古城小镇或是从文先生的《边城》便志于此往往都过于单薄。
当真正踏上旅途的时候,反而没有了任何的激动,激动都给予了以前,有的只是闲适的期待,至于期待什么,自己有些模糊,美丽的古城小镇?至纯至朴的民风?浓厚的人文气息?抑或是有点夸张的诗情画意?还是藏在心中一些模糊而又不大好意思或者说不好表达的一些情绪?还是非常官方的说:兼而有之?
颠颠簸簸,几度转车,实现了千里位移的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下车的地方在古城中的小桥,位置较高,一番灯红酒绿尽收眼底,脚下用潺潺或者汩汩形容都不大合适的河水,一阵甚带寒意的微风,甚为潇洒的小雨,我尽情的深呼吸了一口气,拼命的,狠狠的,好像是这个地方欠了我的一般,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深呼吸却又好像不是很特别,还有则是这就是我脑海中翻腾了很多遍的去处?
有点儿像,有点儿似曾相识!
一动情,我给几个好友发去这样的短信:
夜至边城,于沱水之畔,把酒酹江,吸天地之灵气、揽日月之精华,暮雨如织,灯火阑珊,枕于老先生之侧,《边城》的边城,斜帘挑处:有凤曰凰,一页风景美如画。
——某于湘西沱江之侧吊脚楼下。
在沱江边上沉沉的睡去,带着诸多的疑问、忧虑,尔后缓缓醒来....
到凤凰的第一个早晨,出了所住的居所——站在河边,我再次深深地、狠狠地、用力的呼吸了一口气,然后转了好几个360度,目力所极之地,都好好浏览一番,不用思考的念出一句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近看遥却无。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远处略有薄雾,够不上了烟霭纷纷的场景,但很自然。
长而狭窄的胡同,那些用于江南的诗句毫不别扭的可以搬过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巷子狭窄,人不多,故没有仄逼之感,因为是大清早,往来的多为一些苗族老人,之所以知道他们是苗族老人是因为他们较为特别的着装尤其是一顶大且高的帽子,除了老人便是小孩居多(后来听当地人讲,年轻人大多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可能是来这个地方旅游的人太多的缘故,对于到这里的各种服饰不同年龄的人并没有太多惊异,很多小孩都戴着红领巾,更是显得与外面的小孩无异。
再说说老人吧,在这里的老人基本上是上了年纪的,走路都比较慢,衣着朴实,一般以蓝色为主,额头和中国成千上万的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一样——有着层层的皱纹,皮肤颜色较为灰暗,和褐色的地面石砖颜色相称,一道道的皱纹仿佛细数着这个小城的年月——就是这般如皱纹一样——层层累叠起来的。
之所以反复提到这群老人,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就是他们才是这座小城的创造者和守望者,他们看惯了太多的人来了又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孩子都离开了这个别人都想来看看的地方,以至于老人们对于造访者没有太多的表情。可是,这群老人并没有因为古城的旅游业兴旺而富裕起来,他们在这个地方过了几十年,忽然什么都变了,以前那种宁静的、封闭的,哪怕是无知的愚昧的生活——不管怎么说——被打破了。年岁已高使他们无所适从,至少他们没有能力在河边建旅馆、在沱江里当艄公来供游客观赏沱江,没有年轻人那种致富的精力和头脑的他们却还要生活,以前可能生活的穷一些,至少自己没有抱怨多少,可是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却要为生计奔波了,去过凤凰的朋友都不会忘记,在街边,在河边,在很多景点的角落,又这样一圈老人,默默守着自己的地摊,上面有自己做的银器、红花、刺绣等很多东西,他们并不像那些中年人和小孩一样的叫卖或者拉着你请你看看,在一个苗族老人的地摊前,我发现一个老人手里捏着针线,但耷拉着头,很显然已经睡着了。那一刻我的新明显的收紧了....我想到了她的老伴,是否等在家里等着她的的归来或者缓行在接她路上,或者一样在等下打盹儿?
蓦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们可能都不在人世了,这个小镇的一群最具代表性的最忠实的守望者不在了,他们很多都是沈从文当年笔下的小孩。这一群老人是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后一群老人了,等到下一与时俱进代老人来临时...
于是,我们就这样漠然的在他们旁边走了那么多回...
凤凰的景色,动辄万言,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却觉得没有必要发挥这个主观能动性了,过目的就在自己心中了,自认为我言不能尽其美,故不弄巧成拙。
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黄永玉故居,古城内的城门楼,祠堂,的确沉浸了千年的气质,在他们的故居,在他们曾经走了无数次的青石街道上,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余秋雨先生在巴黎、迈锡尼、弗洛伦撒都曾思考过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如此密集的出现如此之多的影响文化史的人?此言退一步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小小镇子这么密集的出现了这么多影响了中国文化史的人物?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广而言之呢,在距离这个地方很近的地方还出现了宋祖英、王志,地域时间,无不接近。
在沈老先生的房子里,给人感觉到的是一种逼人的、压抑的感觉,那么多著作被简单的摆在了一个玻璃柜子当中,那么密集,那么惶惑,惶惑什么呢?其实老先生的这些书在这里是无法找到归宿的。我为此做了一个实验,我先后问了好几个上年纪的人:辰溪(我自己也不甚确定有此一溪,但又觉得大抵不会错)在哪儿?茶峒在哪儿?何谓走水路?这可是沈从文自己写出来的啊,诚然,成文于北京,但谁能否认《边城》里面的一丝一丝的情怀是积淀于这个小屋呢,荡漾在当年清澈见底的沱水之畔呢?
三个问题的答案依次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以至于我丧失了去问年长的老人的冲动和勇气,行程安排之故,没能去老先生的墓地,马上就是清明节啊,会有很多的人和我一样,带着他的《边城》或者边城情怀,我自认为比较虔诚,带着老先生的《边城》和其子沈龙朱先生的《凤凰于飞》,却不曾去其墓地跪拜一番,憾也!愿其泉下无知,否则,他会更孤独!
在凤凰真正带了两天,基本上是阴雨天气,很多人为我感到遗憾,我坦然一笑,晴天有晴天的风致,雨天有雨天的情调。
在凤凰的两天,伴随着天上的大块乌云、灰蒙蒙的天空,我就索性低着头在街道上行走了,看着青石板上的花纹,有规律的斜纹....
上天有时候是眷顾行客的,走的那天早上,碧空万里无云,直抒胸臆压抑之感,灿烂的阳光洒在潮湿的凤凰,远处,真正是烟霭纷纷了。
因为是淡定的来,所以淡定的走,有过波涛汹涌的感觉,有过那种文人气质特甚的时候,都留在了那壶女儿红里面了。那种感觉还是那句话,无法言说,不带来,不带走。
我想起了魏晋时期的嵇康和钟会的对话:
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以此做结,甚妙。因为有约,十年之后,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