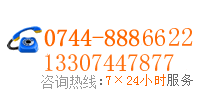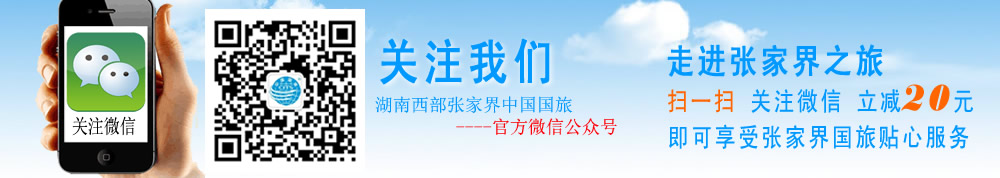凤凰对于我,是沈从文《边城》中那座沱江边的小城。
小河,民居,青石板路,仄仄的窄巷,这就是我心中的凤凰。
头顶上戴着繁星,我们从武陵源上路了。
我努力让自己忘掉张家界金鞭溪两岸的石柱危峰,忘掉黄石寨与袁家界奇峰怪石,忘掉宝峰湖的高峡耸峰与龙王洞的鬼斧神工,我要清空自己一路上看到的所有美景,为的是装下凤凰的古朴。
近四个小时的颠簸,我没有一丝的困意,脑海中兴奋地搜寻着《边城》里的每一字。沈先生文字中的湘西是遥远的、飘渺的,神奇的,此时对我而言,也是触手可及的。

天刚亮,导游便指着远处山上层层叠叠的屋顶说,那里就是凤凰。它静静地偎依着青山,脚下淌着潺潺的溪流,薄薄的晨雾中似乎也溢满着诗情画意,每一寸泥土都浸透着诗化的气息。
凤凰城是朴实的,少有新兴古镇媚俗的面孔。走进小城,随着早晨暧昧阳光带来的,是淡淡的烟煤味。烟煤的味道懒洋洋的,弥漫在小镇的空气中,带给我的是亲切感,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街上的房屋是破旧的,商店里面是灰暗的,阳光透过遮阳篷投射到地面上,斑驳一片。
我喜欢清晨的边城,没有游客的喧哗,没有商家的吆喝,看着沱江边的吊脚楼与江上的小船,心也逐渐静下来,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无谓的纷争,清晨的凤凰,像浅浅的溪流缓缓淌过心田,荡涤了尘世的尘灰,心情因此多了很多别样的韵味。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半夜启程的原因吧。
青石窄巷与沈从文故居
走在通往沈从文故居的窄巷里,两边尽是屋檐下的木制招牌、雕刻在窗棂上漂亮的花格、还有重檐青瓦的一间间老宅。古巷两旁的店铺透着色调平和的光线,门框上成串挂着草鞋与各色的扎染,与那落满灰尘的农具一道,绊住了我流动的思绪和目光。
巷边暗暗的角落里,穿着粗布衣服的老人缓慢地从幽深的宅院里踱出来,坐在树下阴凉的暗影里,看着江水映射着天上的云影霞光。
走进弥漫着淡淡芳香气息的沈从文故宅。
展架上沈先生的手迹流畅、飞扬、洒脱,抓住了我的思绪。先生的故居像他的人,也像他的文章,都是那么的朴实,没有奢华,没有媚俗,没有雕饰。
回头看看攒动的人头,看着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刚买来的《边城》或是《湘行散记》,感觉似乎买了这些小册子便能体会小城的气息,或是沾上文人的神采。我笑了,想起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不是我,是风》。这风想必也会吹到天堂,相信沈先生在天之灵也会笔笑着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喜欢导游说的一句话,“他不是过客,他是凤凰的归人。”
出了沈宅,又来到了青石窄巷深处。在我的印象中,从这里走出的文人,不仅有沈先生,还有黄永玉这位艺术大师。也许在这窄巷的另一头,在某个隐秘的天井里,还埋藏着其它名人的故事。也许这便是我们从千里之外来到这个群山环抱中小城的全部理由。但是,我们不可能占去凤凰的整个灵魂,古城的主角仍然是那些世代居住在此的凤凰人。在那些其貌不扬的窄巷里,时常看到许多老翁在读史吟诗,许多老太太坐在自家门槛前纳鞋底、刺绣。他们每天守着时光像江水一般不知疲倦地从吊脚楼枯瘦的支柱间流淌,就像我们在城市里等着时间从指间慢慢滑落。他们是那样惬意和自在,不理尘世的人事沧桑,不理会游客猎奇的嬉笑。那情景仿佛在告诉人们,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古来如此,以后依然如此,流动的是人,不变的是气质。
沱江与吊脚楼
和古城城内相比,沱江显得异常清新,空气中的烟煤味似乎消散了。眼前是青山和碧水,岸边是青石板的堤岸,水中是整齐的石桩,石桩上走走停停的有外来的游客,也有当地的居民。石板是湿湿的,石板的缝隙中不时可以看到几株水草,绿绒绒的,活泼得很。就这样走着看着,我们上了船。

船家不停地摇动船桨,水在桨的搅动下哗哗地响,那种看似简单的节奏足以驱除心中大多的杂念,只觉得心静神明,清风轻柔地拂面而过。城里与岸上如梭的游人打乱了古城的宁静,但是,这桨声又给我带来了另一种静谧,直到这里,我才感受到古人所说的“欸乃一声山水绿”的意境。
船下,水底簇簇密密生的水草在慵懒的水流中舒展着自己的筋骨,几只白鹅在平滑的水面上自在地游弋,你来我往的游船在并不算宽的江面上穿梭,河面上闪动的是层层的涟漪。哀怨的氤氲像那炊烟,弥漫在沱江江面,久久不肯离去。
两岸便是吊脚楼群了。
想观赏吊脚楼的风韵,最好在水上看,在岸上是看不到全貌的。凤凰的吊脚楼临河而建,一半在岸上,靠山石依托,一半在水中,靠几根木桩支撑着。两岸的吊脚楼传承了沱江江水安份、平和的秉性。从船上看,它们更像士兵组成的列阵,一字排开,正向船中的人们致敬,你靠着我,我挨着你,静立中显露出倾斜。那些粗细不同,高矮不一的木桩,像一个个赤裸着上身的精壮汉子,把坚实的双腿插入江中,用臂膀担起了整个古城的重量。
在充满雾气的河面,橹声浮动,一切都荡漾在黄昏金灿灿的光芒中。不远处,便是黄永玉的夺翠楼。它像一个耸起的龙脊,从老街伸向沱江,将吊脚楼群整个撑了起来,挽住了那里旧的传统和新的典范,相映相伴,相依相偎。
慢慢游动的岸上,除了背着背包匆匆的游人,便是一个又一个,一拨又一拨浑身布满大大小小的口袋、扛着三角架与相机的摄影师,或梳着奇异发型又肩背画夹的写生者。这些匠人们,使出浑身所有的解数,抢占着自认为最佳的地形,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心境欣赏着沱江的美景被江水的美丽陶醉着,感动着。
就是这舒缓明澈的和宠辱不惊江水,赐予凤凰人才华与魂魄,才使凤凰人有着江水一样宁静、淡泊、从容的性情。每一个喜欢沈从文作品的人,只要走近沱江,用心地观察、感悟,就会找到大师文章中的人物原型和生活场景。或许给你指路的婆婆,正是书中的翠翠,或许那位在码头摆渡的老人,正是傩送。
我在岸上的行人中寻找着,看看是不是有相似的原型。看着岸上穿着土布衣裳的当地老人们,我不禁痴了。就像书中所言,“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眼睛湿了:凤凰,还是那座边城;凤凰,仍在讲述着那个不说爱的爱情故事。
上了车,离开古城。戴上耳机,刚好是那首《等等等等》:
这原是没有时间流过的故事

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
翠翠和她爷爷为人渡船过日
十七年来一向如此
有天这女孩碰上城里的男子
两人交换了生命的约誓
男子离去时依依不舍的凝视
翠翠说等他一辈子
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
等到黄叶滑落
等等到哭了为何爱恋依旧
她等着他的承诺等着他的回头
等到了雁儿过
等等到最后竟忘了有承诺
一日复一日翠翠纯真的仰望
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
那年头户对门当荒唐的思想
让这女孩等到天荒
那时光流水潺潺一去不复返
让这辛酸无声流传
路易·艾黎说,“中国有二个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一个是福建长汀。”
下一个假期,希望我仍在路上,在长汀。
|